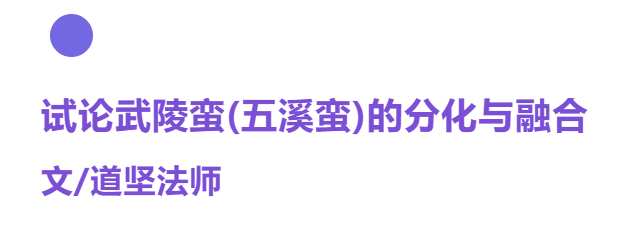
武陵蛮(又称五溪蛮)作为武陵山地区早期族群共同体的核心载体,其发展历程贯穿武陵郡建制沿革与区域民族互动全过程。从先秦时期的族群聚合,到唐宋时期的民族分化,再到元明清至今的多元融合,这一过程既是地域族群自我演进的必然结果,也是中央王朝治理与族际交往互动共同作用的产物。本文以民族学视角梳理武陵蛮的分化脉络与融合路径,剖析其从模糊族群共同体到多元民族格局的演变逻辑,揭示这一历程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根基。

一、研究脉络与学术基础
武陵蛮(五溪蛮)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,经过百余年发展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格局。早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先对武陵地区民族进行实地调查,开启了该领域的现代学术研究范式。国内学者凌纯声、芮逸夫在民国时期对湘西苗族的系统考察,其成果《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,明确了苗族与武陵蛮的族源关联。
新世纪以来,研究维度持续拓展。黄柏权、杨亚蓉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,系统梳理了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机制,强调移民与土著互动对民族格局的塑造作用。杨洪林、龚义龙等学者聚焦移民史研究,揭示了汉族迁入对武陵地区居住格局、经济形态与族际通婚的深刻影响。同时,艺术学视角的介入丰富了研究层次,杨洪林、樊祖原通过织锦技艺演变证实土家族与苗族的文化互动渊源,王平、刘琪则借助戏剧曲艺解析民族文化融合的微观过程。分子人类学研究亦提供了新证据,证实苗族、瑶族、畲族同源于武陵蛮的早期分支,为族源分化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撑。
二、武陵蛮的族群起源与早期聚合
武陵山地区的族群积淀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高庙文化时期,洪江高庙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该区域早期人类活动的连续性。先秦至两汉是武陵蛮族群共同体的形成阶段,这一时期的族群聚合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从族源构成看,武陵蛮并非单一族群,而是多元土著与迁徙族群融合的产物。考古学证据显示,沅水流域存在两类核心文化遗存:一类是以石门皂市遗址为代表的、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的土著文化,对应从洞庭湖迁徙而来的三苗族群,构成苗族先祖的重要来源;另一类是以桑植朱家台遗址为代表的本土文化,为高庙人后裔所创造,成为土家族的远古根基。此外,巴人、濮人等族群的迁入进一步丰富了族群构成,形成“蛮”系族群的多元融合体。
武陵郡的设置(汉高祖五年,公元前202年)成为族群认同凝聚的关键契机。两汉时期,生活在沅水中上游雄溪、樠溪等五溪流域的族群,因隶属于武陵郡而被统称为“武陵蛮”,又因核心活动区为五溪地带而得名“五溪蛮”。这一时期的武陵蛮虽保留浓厚的原始社会特征——如以鱼肉类糅合祭祀的图腾崇拜习俗,以及“木皮织绩”的原始生产技术——但已形成初步的族群认同,其活动范围以武陵郡为核心,涵盖今湖南常德、怀化及黔东、鄂西部分区域。
三、从族群共同体到多元民族雏形
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是武陵蛮分化的关键期,在地理阻隔、迁徙流动与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,模糊的族群共同体逐渐拆解为多个具有独特特征的民族雏形。这一分化过程呈现出“核心区域固化与边缘迁徙分流”的双重特征。
苗族的分化成型具有代表性。汉光武帝时期的重兵征讨引发武陵蛮第一次大规模迁徙,部分族群沿乌江西上进入黔西北、川南。唐宋时期,“苗人”称谓开始在文献中出现,标志着其从武陵蛮中正式分化。湘西、黔东形成稳定聚居区,腊尔山地区逐渐成为苗族核心聚居地,其“顺着日落的方向走”的迁徙传说,印证了这一过程的艰辛。明代“红苗”支系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苗族的族群边界,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的“镇筸苗”成为朝廷治理的重要对象,其反抗活动贯穿明清两代。
土家族的形成则呈现“土著根基与制度塑造”的特点。作为高庙文化后裔,土家族先民长期定居沅水酉水流域,五代至宋代被称为“南北江诸蛮”,“土人”“土兵”等称谓逐渐固化其族群标识。唐末五代羁縻州的设立加速了其分化进程,土司制度的萌芽使土家族形成“田丁”依附领主的社会结构,与苗族的社会形态形成显著差异。值得注意的是,土家族虽为本地族群,却较早受到汉族制度文化影响,为后续融合埋下伏笔。
瑶族与畲族的分化呈现迁徙驱动特征。唐宋时期,部分武陵蛮族群沿南岭南下形成瑶族,东迁湘东则发展为畲族,完成与苗族的最终分流。瑶族“莫徭”的古称与山居文化,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。这一时期的分化并未导致文化割裂,各民族仍保留着“合款”“议榔”等共同的社会组织形式,体现了分化中的文化延续性。
四、多元民族格局的稳定与发展
元明清时期,中央王朝治理政策的深化与族际交往的频繁,推动武陵地区从民族分化转向融合共生,最终形成稳定的多元民族格局。这一过程以制度变革为牵引,以经济文化互动为纽带,实现了“多元并存与一体认同”的辩证统一。
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构成融合的制度背景。元代将苗族地区封建领主纳入“长官司”体系,明代进一步完善土司治理,使领主经济达到鼎盛。但土司的割据性也阻碍了民族融合,黔东南“爷头苗”与“洞崽苗”的等级界限、黔西苗族对彝族土司的人身依附,反映了封闭状态下的社会分化。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打破了这一格局,虽伴随武力冲突,却彻底瓦解了领主制,推动地主经济发展,更打破了苗区的封闭状态。湖南城步苗族地区自弘治十五年(1502年)率先推行改土归流后,农业技术显著提升,铁质农具广泛使用,银饰锻造、蜡染等手工业蓬勃发展,为族际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。
经济融合构成民族共生的物质基础。玉米、红薯等外来作物的推广解决了喀斯特山区的粮食问题,使苗族等族群从渔猎采集转向定居农业。定期集市的兴起成为族际交流的重要平台,湘西、黔东南的苗汉交易市场不仅流通粮食、食盐等生活物资,更促进了“溪布”“点蜡幔”等民族工艺品的传播。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木材贸易更形成跨区域经济网络,使各民族在经济依存中深化认同。
文化融合体现为“互鉴共生”的鲜明特征。王阳明心学通过庞溪书院等载体传入武陵地区,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对话。土家族的“打喜”仪式吸收了汉族礼仪元素,苗族蜡染技艺融入汉族图案风格,体现了文化融合的主动性。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,虽使土家族出现一定程度汉化,但也催生了“苗汉杂居”“土汉通婚”的普遍现象,形成“你中有我”的居住格局。这种融合并非单向同化,而是各民族在语言、习俗、信仰等领域的双向借鉴,如苗族古歌融入汉族历史叙事,汉族节日吸收苗族歌舞元素。
现代民族识别与政策保障巩固了多元格局。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中,田心桃等代表的积极推动使土家族从隐匿状态中被正式确认,与苗族、瑶族等共同成为武陵地区的主体少数民族。当前,武陵山地区形成苗族、土家族、瑶族为核心,汉、仡佬、侗等民族杂居的格局,各民族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”,构成民族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。
五、分化融合背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
武陵蛮从分化到融合的历程,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地域层面形成的微观缩影,其蕴含的历史逻辑为理解民族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辩证统一贯穿始终。从两汉武陵郡设置下“武陵蛮”的群体标识,到唐宋羁縻州制下的族群分化,再到元明清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中的国家治理深化,武陵地区族群始终在“地方认同”与“国家归属”的互动中发展。明代苗族起义虽反抗压迫,却多以“诉求公平”为目标,最终融入国家治理体系;改土归流后各民族主动接受中央政令,体现了国家认同的深化。
文化多元与价值共识的形成奠定认同基础。武陵各民族虽有独特文化标识——苗族的古歌、土家族的摆手舞、瑶族的盘王节——却共享“勤劳坚韧”“重义守信”等核心价值,更在长期互动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。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文化生态,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。
族际互助与命运与共的实践强化共同体纽带。历史上,武陵各民族在反抗压迫中多次联合行动,如元代九溪十八峒诸蛮共同抗元,明代吴天保起义中苗、瑶、侗等民族的协同作战。当代脱贫攻坚与区域发展中,各民族的互助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命运共同体意识,印证了武陵蛮分化融合历程的当代价值。
六、结 语
武陵蛮(五溪蛮)的分化与融合历程,是武陵山地区族群在三千年历史中不断调适、演进的结果。从先秦时期的多元聚合,到唐宋时期的民族分化,再到元明清至今的融合共生,这一过程既遵循族群发展的内在规律,又深受中央王朝治理与族际互动的外在推动。学术研究已通过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证据,清晰勾勒出这一演变轨迹。
这一历程的核心启示在于:民族分化是族群自我认同的必然阶段,而民族融合是多元互动的历史归宿。武陵山地区最终形成的稳定民族格局,既保留了各民族的独特性,又强化了共同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基因,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佐证。在当代语境下,回溯这一历史过程,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。

